在很多人看来,自由主义这一现代性思潮是自然而然的要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划等号的。这不仅仅是由于自由主义否认任何优先于个人的集体国家观念,更是因为在自由主义的谱系中个人权利是至高无上且普世通行的。既然生命权,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等基本权利在自由主义里是不分国别的被人人平等享有的,那么以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者就不应该有任何自身的国别偏好,自己也就该是个彻底跨越国家界限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而在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思潮之所以不可接受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其理论核心彻底抛弃了任何国家认同的观念。自由主义者也就因此被他们打上了“叛国者”和“卖国者”的符号标签。
那么自由主义是不是真的无法推导出一套完全符合自身原则的国家认同观念呢?可以多少肯定的是缺少一套国家认同观念的自由主义必然会在传播和推广上遇到困难。除了文化保守派对自由主义无视国家情感的批评,现实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多少有一丝爱国情感,一个完全缺少国家认同的自由主义也就因此难以与他们产生共鸣。简而言之,国家认同观念的缺失已经成了自由主义的一个软肋,也是自由主义者在论证自己理论时所要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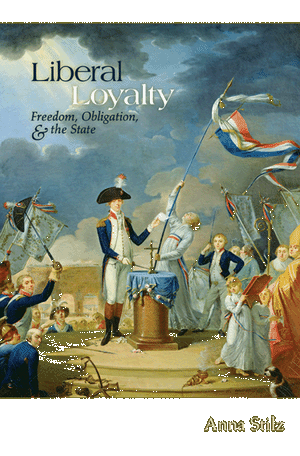
而由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学副教授Anna Stilz 于2009年所著的“Liberal Loyalty: Freedom, Obligation, and the State”一书就旨在解决自由主义者所面临这个难题。在Anna看来,自由主义不仅可以拥有一套完全符合自己核心原则的国家认同观,而且这套自由主义式的国家认同观在理论上比其它任何非自由主义的国家认同都要正当和符合逻辑。
而在讨论这套自由主义式的国家认同观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自由主义不可能支持甚至要批判何种的国家认同。自由主义当然不会允许以国家情感为掩护的专制统治,它不可能认可荒唐的“爱国=爱政府,爱朝廷”。自由主义还不会同意任何基于文化民族情感的国家认同。这一方面是由于自由主义认可每个个体脱离/加入某一文化群体的自由(而不像传统主义和社群主义认为人生下来就必须归属于某一文化群体,没有自我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大多数为多民族/文化国家,基于某一文化的国家认同往往会带来一国之内主流文化民族群体对于非主流文化民族群体的种族/文化/信仰歧视,有悖于自由主义的人人平等观念。何况文化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不完全重合也是不争的事实,以对某一文化和民族的归属感推导出一套爱国情感在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按照这个逻辑在中越边境受越南风俗文化影响的中国人该爱越南而不是中国,中国的朝鲜族人该爱韩国/朝鲜而非中国)。
那么在排除了政府和文化民族的爱国观念后,一套完全自由主义式的国家认同到底又是什么呢?Anna Stilz在书中给了我们两个答案:一套自由主义式的国家认同既可以是基于启蒙运动集大成者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的权利捍卫国家认同,也可以是依靠当代法兰克福学派旗手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政治参与国家认同。
我们不妨先来看康德哲学的国家认同。根据康德的逻辑,每一个公民应该有一种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认同归属感是因为每个公民的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需要国家机器去捍卫和保障。如果国家实现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充分保障,那么公民就应该“投桃报李”的对自己的国家有归属和认同感。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并不是对自然状态下人人自危充满暴力恐惧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国家的必须在康德这里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相信人性本恶,无政府状态人们时刻面临他人的暴力威胁。康德认为即使人性本善,那么国家对于捍卫个人权利依旧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国家,那么个人权利的实现完全就要基于另外一个个体的判断,即使这个个体本身没有恶意。即便个体不想从别人那里获得非正当利益,个体判断行为本身在康德眼中就构成了对个人自由不可饶恕的侵犯,因为它让我的权利受制于你的价值观念,让我由此变成了你的“奴隶”。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国家成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方法。在自由主义国家里我的权利受制于我自己拥有政治话语权的国家机器,我的行为等于变相臣服于我自己制定的普适性法则,我就因此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康德式的个人自由。
而如果说康德权利捍卫式的国家认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极的认同(我认同我的国家因为且仅因为我需要我的国家来保障我的权利),那么依靠哈贝马斯沟通理性建立起来的政治参与式国家认同则是一种积极式的国家归属感。根据这种诠释,如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虽然被自由主义认定为普遍有效且人人平等享有,但这些权利本身却是抽象而非具体的。这些权利的真正实现则仰仗于公民通过沟通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参与政治活动,用法律的形式将权利实现的具体途径和方式规定下来(比如财产权牵扯到具体的商业交易法律和知识产权法律,生命权牵扯到是否基于对生命的尊重建立全民医保体制等等)。这样一来,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就不是单纯靠被动的等待权利被国家机器保护来消极实现的,而更是靠积极的政治参与,通过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等形式寻找更好更全面的权利实现途径获得的。这也就成了因同属于某一不断自我参与的政治共同体而产生的积极国家认同。
总的来说,自由主义者可以有一套完全符合自由原则的国家认同观念,他们并不需要全部成为毫无国家偏好的世界主义者(虽然自由主义本身不批判个人的世界主义选择)。这种国家认同观念既避免了打着国家情感旗号侵犯个体权利的威权/极权统治,又避免了文化/民族感情带来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有条件的国家认同。换句话说,一个自由主义者虽然能够同意一定程度上的国家认同,但他或她很清楚这种认同的根基何在,即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在他或她看来,一个没有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国家的国家认同和爱国情感都是不具有任何道义上的正当性的。
本文原载于“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号:wethinker2014),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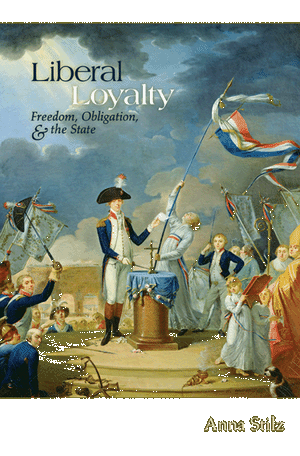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